採訪 / 高友儀、陳詠佳、顏彣晴
 曾御欽
曾御欽
Tseng Yu-Chin
曾御欽,人稱「毛牛」,影像藝術家,曾獲邀參加德國第十二屆卡塞爾文件大展, 是近五十年來唯一參展的台灣人。曾任實踐媒傳系講師、北藝大教師。
「我的人生際遇其實蠻戲劇性的,它沒有乖乖地說我一定要幹嘛。
我的個性又比較溫吞,在對自己的未來這件事情,一路遇到很多老師、很多人,才決定要做什麼事。」在實踐唸書的時候,我沒有想過畢業之後要當藝術家,(當時想要做的是設計師,到五十歲開一間咖啡廳,現在是提早了十年這樣子,沒有想過自己又回到小時候想要當藝術家的狀態。)念到後來就遇到陶亞倫老師,他有一堂課叫存在主義課,你要做什麼都可以,剛好我爸送了一台很小的 Sony 的 pc205 的掌上型 DV ,卡帶式的,算是他支持我繼續做我想做的事情,那我就開始拍片,一直拚命地拍,陶老師看到之後偷偷拿給北藝大的老師。陶老師跟我說「毛牛,北藝大開了一個新的系所之類的,你一定要來」我問他是什麼,他說你先來,我那時候連什麼是藝術創作什麼是錄像藝術都不懂,進了研究所是袁廣鳴老師面試的。實際上我進去以後,他就指著我說你一定要做錄像,「蛤?甚麼是錄像?」我完全不懂,完完全全不懂。
其實是他半哄半騙才會進北藝大,所以我的藝術生涯是這樣開始的。
著迷動態影像,才走上創作?
應該說,那時候我很相信藝術治療這件事,我人生發生很多私人的事情,又沒有很好的生活狀態,所以就乾脆投入在創作裡面,執意在創作這條路上,覺得說真正可以跟我對話的就只有創作,拚命地相信藝術創作可以解決生命的一切,我曾經發過兩次毒誓,一個是我不要再談戀愛了,我要專心創作,我那時候真的是一面哭一面在心裡發誓;第二個就是我不要再相信任何人,我要專心創作。沒想到都讓我得到很好的結果,一次是台北獎,一次是德國文件展。
當時拚命地相信藝術創作可以解決生命的一切,那當然現在我覺得不是,卻覺得說那時候拚命創作,不會後悔。其實我很有自信,我不相信台灣有多少個藝術家有這個能耐像我這樣子來藝術創作。
藝術家創作的使命
在我的觀念裡面為什麼藝術很重要?藝術創作來自於,藝術家很多無以名狀的感受,像是對於生命,深刻的、未知的、生活的感受,我去感受才開始創作。
為什麼會有一個時代出來:藝術家他成為這個時代的某一個環,我做出了某一個影像,拍出了某一張照片,寫出了某一段文字;哲學家看見了,政治家看見了,數學家看見了——他們看見,開始對話,然後彼此揭露了哲學,談到一些新的思想,新的哲學就誕生了,新的理論就出來了,新的時代就出來了。你問藝術家能不能解決社會的狀態,或者治療?有,但這個使命感是不是每個人都了解,沒有。
我之前的演講,有很多那種大庭廣眾就說你們當代藝術家都拍拍生活啊、拍拍自己啊、喃喃自語啊,我就直接回說你聽不聽台北愛樂,他們之前有一個很經典的 slogan :「今日的流行是明日的古典。」請問我們藝術家是不是在做現在的狀態,拉長時間軸,站在未來回頭看,我們是不是凸顯這個時代的狀態?那他是在講自己嗎?例如梵谷畫召妓、畫自己的房子,他是在談那時候的生活狀態,那樣子的社會氛圍,那時候的心理思緒狀態,那樣精神異常的狀態,當時的精神壓迫、社會環境與社會結構。
是不是拉長時間軸看是這樣?已經存在的哲學理論或任何藝術理論,我不是不尊重他們,而是如果藝術家一直追求以前的理論,那新的理論就不會出來了。
相信藝術治療,現在這個想法有轉變嗎?如何看待?
我現在可以回答的是說藝術不能解決一切,藝術創作不能解決你的生活問題,但是他可以梳理,梳理你的生命歷程,你會比較好去整理,一般人可能他的腦袋還沒辦法去處理過往的狀態,可是藝術創作者有一個好處,你們會不斷地梳理你當下跟過去的狀態,不斷地重組跟建構自己,你就會更完整的去生活。所以我說多多少少有一點變,但是也有不變;相不相信藝術治療?相信。但藝術能不能解決一切?他不是治療,因為沒有人是完整的,只能幫助你不斷地梳理生命當中的過程。
佳: 做到後來可能會迷失自己的想法?
會,可是你要不斷地回頭去想。講那個很老套的《迎向靈光消失的年代》,為什麼要追那個靈光,腦子裡一閃而過的靈動是很重要的,你要不停去想那個東西是什麼,去回溯的時候你的作品就會慢慢清晰、清楚。可能是因為我很容易看到你們的沒自信,常常會有一些加東加西的動作,或是說你影像過度處理,很多雜訊一直閃,我會問說你是不是很怕你的東西沒內容,大部分的同學都會說:「對。」都會被我拆穿。
因為你們會擔心自己不夠,因為你們的成長過程一直是被否定的,這就是台灣的教育環境: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…..你終究行但是要等你長大——可是回頭想,我已經四十歲,還是覺得自己像二十幾歲的小孩,我相信所有人都這樣,沒有人準備好當大人這件事情,你們準備好畢業了嗎?你們準備好長大了嗎?你們有辦法想像自己有小孩嗎?沒辦法嘛!你完成蛻變的預期不在階段而在於你自身,所以人不斷地害怕自己的改變,但這個改變永遠都要,你必須要面對,但是不是用制度去面對。
面對別人看待你作品不同的態度
實際上跟你沒有很強大的連結,但是他卻在這讀取到他要的東西,我倒覺得這是一件好事,而且你似乎完成他生命中某些可能性。
每個人都會有詮釋你作品的自由權,別人願意去用你的作品產生對應跟對話,表示你的作品有強烈被採用的可能性跟強烈的對話的可能性(就算你們的意圖不在上面)。其實你們有時候創作會說老師在講的這個都不是我想講的,可是你可以換個角度去想說,其實我的作品無意間有提到這件事,可是不是你想到的。要不要談自由度在於你,但你不能拒絕他的存在。
其實應該說,做作品的時候沒有想到他可以到達什麼樣的程度,程度的意思是說有多少人會去認同或了解。有人說作品完全是自爽,自己做開心就好啦!可是你想,一個作品的完成來自於展覽,為什麼來自於展覽?因為會有人去對話。你們現在因為被封閉在校園,所以對話就產生於老師和同學之間,會產生一種厭惡感,那個厭惡感來自於說老師會不會誤會作品,這有一個階級式的狀態,同學閱讀作品可能也不見得了解,那就在於說為什麼還是要展覽,你們在這邊學習怎麼去面對別人看待你作品的不同的態度,你的從容性在哪裡,不然你出去會整個瘋掉。
我作品在外面,很多沸沸揚揚什麼都可以講,你只能聽到就:「喔…喔…」因為有反應都是可以產生對話的可能,你會發現很多時候狀況是失控的,他們的對應過程不在你的對應過程裡。我的作品在歐洲也有講過是情色,也有被虐童系列的展覽邀請過去做展覽,那你就說你要拒絕嗎?會有人去問說,那你要去展覽嗎?我說那又有什麼關係,我不認為是個問題。我覺得策展人的使命在這裡,我如何去選取藝術作品,然後用這些藝術作品去講一個故事。
友: 儘管那些作品本來不是這樣說的嗎?這樣也成立嗎?
為什麼不能成立?因為在那些對話過程中,跟他想要的部分產生對話,只要藝術家允許這個對談,那就可以啊!只要藝術家不允許對談,當然就不可以。
作品的發生就像一個懷孕生小孩的媽媽,他出社會發生的所有事情你必須要知道,但你不一定要去承擔,因為他會自己長成某個模樣,尤其在時代演進下,閱讀他的方式會不斷地被改變、解讀與討論。要去控制他嗎?不可能,有些策展人看到這件作品,他就是想要去談,他把他的論述給你看,他把他的展覽計畫給你看,你去決定認不認同這個論述發展,因為實際上一個作品不是只有一個對話,就像一個人有各式各樣的面向。你要在家當乖女兒,你要在學校當可能是幹譙型的學生,或是你要在老師面前當好學生,有可能啊!只是你要選擇多向性的時候,就是要選擇作品的多向性!因為有時候學生或藝術家的的藝術創作,會過度執迷在它就是談什麼。
顏: 那這樣就會有點困惑,他就沒有一個本質在?
本質在你自己。為什麼你會像一個媽媽,因為斷臍帶生產的過程只有你清楚,你要談什麼只有你清楚,但永遠會被誤讀。你的作品出去就像小孩長大,一個不斷被誤讀的過程,在生命的過程裡如果有人願意去讀你就要謝天謝地,他只能從你的生命過程中讀取到某一個短暫。實際上,就像我的作品裡面我要講的永遠只有我最清楚,策展人跟我對話的時候他是試圖從這當中找到我的脈絡,有些策展人比較尊重會說:「我在閱讀上看到什麼?」「是不是這樣?」如果有謀合到的我們就會產生對話,但是有些策展人他是比較掠奪式的,說我要談什麼可不可以給我,那你就要思考,你的小孩是不是可以供給這個對話。
你說講虐童好了,那我的作品裡面就算有虐童,你說我認不認同,我不見得認同,可是我講的是什麼,一個心理的折磨狀態,那你說那是不是虐,是虐啊!那你說跟虐童有沒有關係,無關,可是跟虐有關;但要談的時候我不見得要認同這個策展人的全部,而是他如何完成他的論述。我常常講策展人很像一個拼布專家, 蒐集很多藝術家的作品,放進這個展覽,完成他想講的某一個故事。可是因為你們的疑惑是在於說,台灣有一個藝術狀態,很多策展的方式是——藝術家都要講相同的事情。
友: 所以策展人跟藝術家關係是很緊密的?
應該是很疏離的才對,這樣才能對話。過度了解對方的生活,就會過度貼近,不是貼近作品,而是貼近人物,要有一定的疏離性。我了解你這個人不見得了解你這個作品,就像你們同學之間互相了解但是你不見得了解他的作品,因為你們靠得太近,反而會忽略這個人,就像我講的,過去之種種造成你現在的生命。
走偏的刻度
我很在意自己的脈絡,但是我不是很介意整個藝術圈在發生什麼事情。那時候常遇到在藝術圈的同學或是藝術行政,問我那種大佬型或是前輩,我說我不知道,他們就說:「什麼?你居然不知道?」大驚小怪。好像你十惡不赦、就是壞人,對我該死、有沒有牆我去撞牆。這些是台灣藝術圈奇怪的現象,等我有一些成就之後就說:「沒關係你是藝術家。」突然意識到台灣藝術圈的不健康,你會覺得莫名其妙、會容易迷失掉你自己,這就是台灣狀態。
我以前有一件作品,從德國文件展回來,那件作品實際上完完全全在反駁這些,因為你漸漸迷失掉自己。但藝術生活本來就該自由奔放、該忠於自我,是我應該嘗試去思考怎麼活,經由自己的脈絡去談事情,不知道為什麼,你必須去討好整個藝術制度,變得在服務對外的狀態,而不是服務於作品本身的時候,你根本就消失啦!藝術家就變得很有趣地在論述作者已死,但是台灣形容作者已死不是這樣吧!作者已死不是作者真的死了,而是在位不在位的問題,全世界的藝術圈都有這個問題,如何讓藝術家生活在比較自我的環境下?要讓台灣藝術家生活得比較自我是相對其他國家更困難的。
友: 在未來有可能改變嗎?
我覺得不可能,我的觀念比較悲觀,因為台灣是島國文化,島國文化裡,基本上是不會允許有第二個聲音,大家會害怕對話的時候產生裂痕,一定要忠於某個人的對話、論述這樣子。做作品到現在我在觀察這個生命、生活,已經被多少的人誤解成我的作品在喃喃自語、是在講自身的狀態,這個誤解說來,代表我這個人徹徹底底不存在啊!當我要談一個外部問題時,自己的自處狀態是不是很重要?
我常常會問,一個藝術家要談外勞、一個藝術家要談社會階級;那請問一下你這藝術家是誰?談論這些的人你們是誰?你們有資格談他們嗎?你們如果就這樣大喇喇接露一切,這是不是一種歧視?有多少人談完這些,後來跑去學瑜珈學佛,吃香喝辣,他們有幫了這些人嗎?這些人還是過那樣子的生活。那有人會問說那這樣很弔詭,難道我們就不談他們了嗎?不是!你們到底怎麼談他,你們和這些人的關聯是甚麼?如果只是做一個田野調查、分析解析給大庭廣眾知道,這些人就像你們剖屍的過程,看他們有這樣子的肌理,這樣子的脈絡,這些大眾只是在看一個奇觀。
進入藝術圈
藝術系統的完整性,就是說像台灣藝廊也是各自有各自的狀態,各有各的規矩。實際上很多國外藝廊分很多階層,我可以做到什麼樣的藝術家,我可以跟這個藝術家同時並進到什麼程度;實際上國外有這個系統,但是台灣沒有這樣的概念,這就是它比較大的缺失,沒辦法很完整。其實藝術家很難去別的國家,你看國際上所有知名的藝術家都跟自己的國家有強力的連結,就算要叛逃,也要有一個國家可以逃。
自己的國家沒有全然的支持,是因為台灣很怕獨厚某人,但實際上還是獨厚啊!卻變成我們在國際上很難有一個地位,因為國際上談論的是社會背景、你跟你的國家、你的生活背景;你看見的是什麼?為什麼出去之後比較難發展?這個國家、這個人的生活,就是比較無解的沉重。
其實現在你們也看到了,這根本不需要我講,你們也看得到台灣目前的亂象,會有點迷惑。我常常覺得說你們要在藝術圈創作,所以大一我很多暗示的話,你們漸漸會懂,那時候沒有講白,因為你們才大一經不起這樣的摧殘。
是很悲觀,可是有時候,如果你真的可以去了解這些狀態就不會那麼辛苦,不是說我就叫學生不要做創作,而是你可以持續創作,可是這些持續創作的狀態裡面,不要把得失心放太重。
友: 因為藝術本質不是用錢或名聲得來的勳章。
對。
新媒體的定義是很開放跟廣闊的?
對,新媒體不見得是用一個很厲害的技術完成這件作品,而是你要用什麼技術去完成你想要講的東西,因為我相信藝術家能夠走到越來越刁鑽越來越個人化的時候,所有的技術都要追不上,那個最無以名狀,最無法形容的狀態,本來就是所有技術、論述最無法追尋的,不然為什麼藝術家要不斷的創作那些無法由別人講出來的東西,他就去寫課本就好啦!
你們常常會被新媒體藝術困住,沒錯,我常常在講,這個系有這個系的迫切性,或自己的慌張,因為新媒體的定位在台灣本來就是很慌的東西,我要如何去定位新媒體很重要,可是我每次都跟同學們說,你們不要去管系上的慌張,因為這個系統有這個系統的慌張性,可是你們是什麼?你們就是新啊!每個世代對於上個世代就是新,你們常用的媒體,對我們來講就是新媒體,理所當然存在在你們生命中的媒體就是新媒體。你要回頭去想,那個迫切性在於你身上,你們有時候在談的時候,還是回歸最安全的方式去談,因為你們知道你們最專長的東西是什麼,不專長的東西是什麼,我也是!我知道自己最專長的東西是什麼,可是你回頭去想,如果我要做一個東西,我要運用新媒體,要回去想我要談的是什麼,再去找,甚至你找到一個完全無法找的東西時候,再去想辦法。
老師如何做選擇?對於這個選擇、現在的生活方式
其實如果是我的話一定會回答我現在在藝術圈的邊緣狀態,不會是主流狀態。一開始教你們的時候就講我是最好的負面教材,所以基本上你們不會再遇到更糟的狀況。現在的生活方式算是一種,試圖在之後的未來尋找一個真正的快樂,因為人對於堅持這件事情的執著,有隨著年華消失之類的,那我的解讀會覺得說我要繼續做藝術創作,有時候堅持不是停留在原地或是停留在某一個環境,而是對於自己生存所做的堅持。
如果講自處的狀態,我會這樣想是因為戴佩妮的新專輯,裡面有一首歌叫〈現在的樣子〉,(原歌詞:「有時候不堅持 就會 隨著年華走失」)我的解讀是如果不堅持創作我就會消失,因此拚命地做作品去和別人溝通、拚命地被看見。但是這陣子又去聽了那首歌,我發現有時候不堅持會隨著年華消失這件事,反而是如果我因為身處的自我過度堅持,你必須要試圖在某一個環境(甚至藝術環境下),堅持擁抱著某一些曾經的光環或是曾經的什麼,我覺得那才是真正的消失。自我的狀態、形體的消失,如果我離一些距離不要那麼靠近,或許自己的自處性會更加完整。你說現在的生活方式,應該就是這樣,就是我選擇了自己能和自己繼續對話的可能,但如果我繼續執迷在某個狀態不放下,那我可能會消失,所以我選擇了這樣的生活方式。
友: 嗯,我覺得老師你做的選擇一直堅持著初衷,還會繼續藝術創作嗎?
我暫時停止創作不是我真的停止創作,而是說我必須要重回我自己的生活,那你說我會不會繼續創作?會,只是不會在這個系統裡面。你們怎麼樣去尋找你們的生活?我常常會提這件事情,要怎麼樣讓自己好過,創作不斷地持續不是為了改變自己,而是在自己的有限當中,找到生活的可能。
有沒有信仰?或支撐你生活、創作的精神支柱,有轉變過嗎?
其實我生命當中常常會有一些小名言,對我自己來講的名言,不見得是對於創作,而是對於我身邊的一些話或什麼。我有跟你們講過「每個年紀有每個年紀最好的樣子,那你就要活出那個樣子。」其實這句話對我很重要;然後還有一句話「別人的好人可能是你生命中的惡人,壞人可能是別人的好人。」就是說你超恨這個人,超討厭他,但他可能是別人心目中的好人;那他是壞人嗎?不見得是,這是一個相對的問題。其實我常常會有這些想法讓自己在生活中可以過的比較順利,我常常跟自己說:「要學會放下跟原諒,是人現階段所有的課題。」就是我如何在現階段學會放下之前的一切,學會誠心的祝福,是我現在要學的。
那你問說有什麼信仰,或許吧!這些信仰是對於生活的歷練,或是我聽到某一句話我覺得對我很重要,我就會反覆背誦,留在心裡,那這些話就對我很重要。就像當別人得罪你,憤恨不平,你恨得牙癢癢,在恨的過程中,別人可能在吃香喝辣;像我以前被欺負,在大學被排擠,我如果就這樣讓自己毀掉,是不是就順了他們的意?他們都不care啊!你為甚麼要讓自己在這樣去care?可是我又講過一句話喔:「你要好好原諒一個人,你終究會原諒一個人。」就像談戀愛一樣,你終究會原諒一個拋棄你的人,那恨他一下也沒甚麼不好啊!其實你們都會知道說長大你終究會原諒一個人,現在不恨他我終究會原諒他,那我現在要幹嘛?人生必經的過程,我要走一遭啊!像同學失戀或什麼來找我,我就說:「好啊!你就好好哭,哭完趕快找下一個。」那你說老師好難過,我會說:「乖,大家都會難過,你就好好感受這個moment,因為你下次被另一個男人拋棄那個難過是不一樣的。」同學說老師你詛咒我!不是,而是這個過程就是這個樣子。
人生命歷程就是要不斷重複一些事情,而實際上那不是重複,因為你每一次經歷都不一樣,所以才會說過去的種種造成我現在的身體,不斷的經歷事情才能有你現在的樣貌,你現在的說話方式。
我覺得人生下來就是在修,而不是去修,就像我不排斥念佛經這些事情,在於說你覺得是好事,但是不能完全去遵循他,我終究會原諒一個人為甚麼不好好去恨他,你要學會那個過程才會放下,我是真的這樣的人,所以我小時候最討厭大人跟我說:「你長大就會懂。」後來你會發現大了也不會懂啊!我快四十了也不懂,有人說生命會越來越圓滿,沒有啊,反而越來越糟,你不會因為長大而產生圓滿。
人家問你到老想變成什麼?我想要變成有故事的人,這是我最終的夢想:如果我老了,沒有錢了,也變醜變皺了,我坐在養老院,可能有年輕人或是護士來跟我聊天,我可以講我七十年來各式各樣的故事——我去過哪裡、做過什麼事、我曾經怎麼樣;我覺得這種人過得很精彩,人要活得有故事。這是我的精神信仰,我不能讓我的生活沒有故事,你所有的過程都可以講,發生什麼事、曾經怎麼樣,所以我才說你們要去多經歷事情,你生命的精彩來自於你本身,所以我在你們大一的時候出作業,回家的路線要一直改,要一個人去旅行,你要學會去製造生活的精采,而不是別人去給你精彩。
在大學的時候有紓壓小癖好嗎?會不會瘋狂的閱讀?
我大學的時候超愛看電影而且超愛看A片,這是實話,我很喜歡那種感覺,就很舒服;我喜歡看很刺激、視覺的東西,以前在實踐,每次大評圖結束回家後我就只看A片,不知道為什麼就會很舒服,他會完全徹底的放空,不會有慾望。平常我不愛看深刻的書,很愛看電影、奇幻的故事還有漫畫,不太愛讀很艱澀的文字,那會讓我越讀越累。
但我很愛看村上龍的小說,《接近無限透明的藍》、《69》和《味噌湯裡》,如果提到這個的話,村上龍的《味噌湯裡》跟《寂寞國的殺人事件》造就了我現在所有的一切,我必須講實話是這樣,因為這兩本書是在我奶奶的屍體旁邊看完的,當時我奶奶去世,守喪時坐在屍體旁邊看著這兩本有關殺人魔的哲學書,其實那本比較像哲學書在討論社會現象,看他怎麼殺人,然後身邊因為屍體會慢慢腐化、脹氣,你會聽到那個屍體發出有點像打嗝的聲音,伴隨著那個聲音慢慢把整本書看完,就變得很深刻。
他裡面說了很多社會的寂寞,實際上那個殺人魔為甚麼會殺人,是因為一個人的寂寞造成了殺人的存在,然後我很相信它裡面講的一個情節:那個殺人魔跟一個日本的導遊說,他住在一個村落,那個村落很純樸,村落裡有一個通往山上的鐵軌;他沿著那個鐵軌走,通向一個湖泊,湖泊裡面有很多天鵝在優游的游著,剛好手上有麵包餵這些天鵝,他想到:「殺死動物是不對的。」他突然想到這句話,手已經扭斷天鵝的脖子,他就這樣看著天鵝,然後走下山,沒有人知道他殺了一隻天鵝。
聽起來好像很無謂的故事,我卻很深刻地記得這個段落,因為他是一個很微妙的段落,每個人的生命歷程來自於你自身,沒有人會知道你發生甚麼事,那個轉折來自於你,要怎麼詮釋就在於你自己本身。這就是我很喜歡這個故事的原因,你們生命中一定發生了某些事情讓你心中產生小小的轉折,可是永遠沒有人知道,因為你會覺得微不足道,但是那個轉折的twist永遠都會記著,很微妙的轉折點,人生命當中身處的尷尬性就是我作品裡面常常講的。
認為在新媒系的學生需要以什麼樣的心態創作?
每一屆大一當然會有各種不一樣的屬性,但你就會覺得說他們就是一半以上很旺盛的想要創作,當然有一些很困惑,當然還是拚命地去做東西,現在看到這些反而是讓我最感慨,也是最警惕的事情——他們維持初衷,你們心目中當時的初衷:「我只是想要做這個啊?為甚麼不能做?」後來再帶你們大三的時候,發現你們心中都有些恨,你們是對制度,對整個藝術環境的執著:「為什麼都是這樣?」然後你們就迷失自己了。
實際上你們也不該就是恨,放輕鬆做,那些疑惑本來就都存在。回歸自己本身,你究竟想要講什麼,我覺得那很重要,不管怎麼樣創作,你自己都不要改變,不過可能終究還是會選擇改變啦…
創作在新媒系產生適應不良的問題,是因為學生表現不符合環境的期待?
(聽過學長有個很可愛的比喻,大意是:新媒系的學生都在海上漂,只管抓住身邊最近的浮木,然後漂啊漂,直到畢業。)
我以前學設計到藝術的時候,學生很容易覺得自己不夠踏實,因為你學幼保系他會照顧小孩,學食品營養系他會食品營養,可是學藝術或設計,能幹嘛?這個問題會產生很多面向,台灣是處於一種否定藝術或是不尊重藝術專業的國家,例如因為影像的快速擷取,我們的手機,幾乎所有設備都離不開影像,所以很多人覺得我也會;實際上台灣對於影像的處理設置是創意的處理,很多人會覺得這沒什麼好厲害的,你們也會漸漸被潛移默化「我好像沒那麼厲害。」因為你們完全是靠直覺去做東西,可能會覺得這是很虛無的事情。這是一個無解,設計甚至時尚都還比較言之有物。
很多學生後來會選擇離開,但是我不反對,台灣環境就是這樣,可是我也常常會講,你要學會讓你自己的身段夠柔軟,我也在學,你們有一身的武功,但是也可以做彎得下腰的工作,可以生活下來,那你問這跟創作有甚麼關係,跟創作無關,可是你們創作到現在都知道,創作已經變成你們生命的必然, 無聊就會創作一下,拍拍寫寫東西,雖然跟你的工作沒有關係。
你們都會迷惘,然後又看毛牛老師開咖啡館,可以不要做了去開咖啡館,我承認我那時候有某方面的執著,過去甚至執著創作是因為覺得還有希望可以繼續創作,那我現在暫時停止創作是因為,我發現我沒有在做我該講的事情。
給想繼續在藝術領域創作的新媒系同學一些話:
選擇自己走的路不要後悔,繼續走下去,這才最重要。你選擇很政治性的對應,選擇台灣當下的藝術創作方式,我常常講說沒有對跟錯你就繼續做下去;當你選擇那樣,或者你像我完全不在台灣體制下繼續做創作,那我也就這樣不後悔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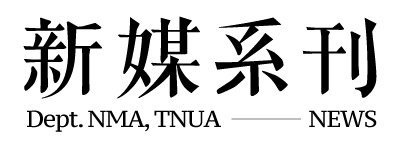

感謝學弟妹與毛牛老師,看到這樣的真誠訪談很感動,如果說唯一感嘆的事情,就是自己的人生路上太少遇到能如此坦承相告的藝術前輩,等到自己發現那些人生或創作的起與落不斷地刻蝕生活時,人已經身在其中近十載…如果藝術本身具有的漂渺與開放特性讓人無從著力,何不趁此放開追求與執著,最後每個人在藝術中照見的是自己。